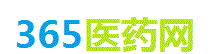随着西迁集结号的吹响,他从上海西迁到山城,从此奉献青春,挥洒热血,用一生践行着对医学的执着与热爱,让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从新生到蓬勃,从微光到巨火,这就是重庆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专家——胡修瑾教授。
本专栏人物推出顺序按照采访视频制作完成的先后,目前西迁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仍在进行,相关采访视频陆续制作之中,《西迁口述实录》专栏将持续推出,敬请期待。
胡修瑾(1934.9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教授
浙江镇海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1958年西迁来渝参与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曾任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伴黄疸的婴儿败血症24例临床分析”“重庆地区小儿轮状病毒肠炎研究”、“华支睾吸虫病”等研究属当时国内先进水平。
动乱年代 九死一生立初心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当时的上海有英租界、法租界,还有中国的地界,我是住在英租界。在亲眼看见了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后,我们住了一、两年就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重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以后,我们又从重庆回到上海。所以我对当时日本人的侵略非常痛恨,也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没用,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因此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一定要强盛起来。
我一岁时得了麻疹、肺炎,很严重,上海所有好的医院都不收治,我是在一个私人医生精心照料下活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完全靠自己的抵抗力,我就这么九死一生过来的,再加上我们家里面的成员也是多病,我的两个哥哥就因病过世了,所以我就想学医。
上医生涯 笃行致远练真章
我学医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我想考的话就要考最好的大学,要考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那个时候出名的医学院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前身,还有就是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等。湘雅医学院和华西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办的,只有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办起来的,而且他的业务能力远远超过了湘雅跟华西。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进学校的时候,国立上海医学院十六个一级教授,有很多大学一个都没有。在全国的大学里面,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一级教授最多学校之一,我又在上海,所以我就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我入校的时候国立上海医学院名称已经改成上海第一医学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术空气很浓,办学非常认真,除了学习业务课以外,还教我们今后怎么获取知识,怎么在知识汪洋大海里用最短最快的办法,找到所需要的材料,那就是文献索引。另外还教会我们怎么搞科研,在课堂学习以外,组织了很多的课外学习,比如说通过学生做科研,来培养我们科研的方法和能力。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德隆教授,他是一级教授,是解放以后从美国回来的,学问很渊博,搞传染病、流行病方面的研究。当时血吸虫病在华东地区盛行,有几千万人得了血吸虫病,由他来牵头带领我们学生一起搞血吸虫病,他是全国有名的教授,毛主席亲自接见过他。
我读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预防卫生专业,这个专业在我考进去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学校对我们很重视,除了课程学习以外,课外跟老师接触非常频繁。50年代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还比较低,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但结论不一定对,老师就要我们来鉴别哪一篇文章结论是对的,哪一篇文章结论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它的科研设计问题出在哪里?统计学应该怎么处理?要我们分析、讨论,这样就培养了我们的科研能力,应该怎么着手,怎么设计,怎么有客观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单位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就要调查第一是不是食物引起的中毒,第二是食堂里面哪一种菜引起了食物中毒?那么科研设计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上医为什么能走在全国前列,一个学校它得留师资、留人才,上医留人才不完全是看成绩,它还看你在科研小组里面的思维能力、科研能力、查文献的能力、表达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样留出来的师资才有后继力。
我在当教务长的时候,留了一些学生,有些学生是高分低能的,因为医学上有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有的同学背得很好,考试成绩很好,但是到实际工作中就没有后继力。有些学生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思维能力就很强,他一到工作岗位上马上就很出众,能把学的各学科知识连贯起来。人是一个整体,他连贯起来以后,思维的方法,治疗的方法,诊断的方法,就突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向上医学习。
潮起远航 踔厉逐梦西迁路
那个时候一切听党的话,我是最后一批来重庆的,前面来的人还开了会,我们后来的就简单了。我在上医工作时,每天十点钟有一个广播体操,有一天做完操以后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就说:“小胡,你要到重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来了。到重庆来,我还是有些思想顾虑的,但是我的顾虑也没有太多,因为我来过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住过两三年,读过书,对重庆有所了解。
来的时候就决定了不回去的。来了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都减少了,我记得我在上海毕业的时候,是拿的五十三块钱一个月,到这里来了以后,拿的是四十一块,降了十二块钱。我们的钱惪院长,在上海拿四百九十九块,到这里来拿三百零九块,降了一百九十块,有的人降十七块、十八块,最年轻工资最低的,也降了十一块钱。重庆条件很差,山下就是南北大楼,周围都是荒地,边上都是农田,大坪到石桥铺这条路还没修好,都是泥巴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生活条件也比较差,来的时候重庆的天气都是四十一度、四十二度,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我们就睡在凉席上,睡一觉起来凉席上就有一个汗水打湿的人影子。然后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半夜三更到下面去冲澡,冲了以后,不揩干就睡了,热醒了又去冲,就这么过来的。
蓄力扬帆 艰难岁月见坚守
来了以后,因为重庆的传染病、地方病非常多,那么学校就成立了卫生系,从一个教研组变成一个系要扩大好多倍。我们原先是一个卫生学教研组,一个流行病学教研组,两个教研组一共来了十三个人,十三个人里面除去技术员,教师只有七、八个人,那么两个教研组开这么多门课很困难,因此我既要教卫生总论又要教环境卫生,还要教流行病,到后来要成立卫生系了,有些专业比如儿童少年卫生,连一个专业人才都没有,当时学校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我去组建这个教研室。前提是回母校进修一年,我就去进修了一年。当时正是灾荒年,政府没有这么大的财力来扩大这个专业,当进修快结束时,重医的院长给我来一封信,说卫生系已经取消了,因为我是学的儿童少年卫生,算儿科系,就让我在上海再进修一年,所以我在母校又进修了一年,就回到重医儿童医院。那个时候的儿童医院虽然环境条件比较差,却是西南第一所儿童专科医院,我们具有上医带来的设备和人才,很快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队伍逐步壮大起来,病人很多,那时有一百多个医生,最有名的医生是石美森、徐谷、沈锦、陈季方……来看病的人大多很穷,我们看病的时候,就要问他你带了多少钱?有些农民只带了五毛钱、六毛钱,那么给他治病的话就根据他的五毛钱六毛钱开药,而且要治好,不是随便开,因为他这个钱来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得知道每一片药的价钱,每种药开多少,加起来多少钱。基本上每天都能碰到这种病人,有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凑点钱给他们。
谋变焕新 创科建系助重医
那时候儿科有一个特点,跟大人不一样,儿科的病大多是急性的,是可以治好,可以断根的,这个很关键,你这个关把好了以后对小孩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儿科医生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的病情从轻到重转换的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早上八点钟看了一个患儿,只是有点儿发烧,跳跳蹦蹦的过来看病,但是假如你没有诊断准确,可能下午一点钟病情就会急转直下,风险是很大的,特别在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期。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病人很多,我们还要看得快,才能够解决病人拥挤的问题。
儿科门诊正常来说一个小时要看十个病人,要写病历、问病史、体格检查、开处方,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十个,快一点的医生可以完成十二个或十三个,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病人。那个时候传染病又非常非常的多,要看得快又不能误诊,所以儿科医生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不愿意看十二个、十五个,我就尽量地看仔细,因为儿科风险大,但是儿科的治疗效果好,治疗了好了就好了。我针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搞了一点科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就是感染性休克,血压可以降到零,很快就死亡,在抢救的过程中,我们统计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九十八,我们团队想了很多办法,搞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措施,最后把死亡率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这个治疗方法在全国来说,我们是独创的。
重医附一院在1970年开设儿科病房,我是儿科主任,当时脑膜炎流行,我曾经成功的抢救回了一例。在所有的药用了以后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后来我就用了一个高血压素Ⅱ,很奇迹的把一个八岁的女孩抢救过来,重庆日报还登了一大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回儿童医院工作,那时非常忙,早上七点半进病房,下午七点半下班,十二个小时里面,吃中饭、吃晚饭都是轮班吃饭,病人都是互相照看一下。在这期间,我要抢救很多重症病人,还要收很多新病人,没有时间写病史,只能下班以后再写,写到十点钟,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辛苦,也不知道外面是春夏秋冬。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传医风
我觉得钱惪院长给人最大的影响是他的作风、他的做人,没有看到像钱惪这么一个高尚的人,钱院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医德的人,不管在上海医科大学,还是在重庆医科大学,他都是得到群众广泛的好评。可以这样说,重庆医科大学能在重庆站住脚,而且发展起来,这都是钱老一生的功劳。虽然我们来的每一个人,重医的每一个职工都有功劳,但是关键的是他把我们组织起来了,把我们(带着)往前走。
来重医以后,他除了抓建院工作、管理工作以外,他还重点抓了一个事情,就是不能把重医变成两个帮,一个四川帮,一个上海帮,对立起来,那不好。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缺少人,每年分派了很多人,华西毕业的,武汉医学院毕业的等,各个医学院都分派了很多人,而且在重庆也招收了一些人,人员就很复杂。钱院长当时每天下了班以后,他都在各家各户串门,看大家家里面有什么困难,吃饭的时候有什么菜,他挨家挨户的走,一直走了几十年。
一个校长,每家每户得走,几乎没有一家他没有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到我家就来了四五次,说来就来。所以现在的重医,人情味很足,四川人跟上海人不分彼此,非常和谐,这个气氛就是钱院长造就的。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细致全面的工作,假如没有他,重医不会有今天这样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来源:党委宣传部
视频制作:陈朝琴 宗华月
编辑:陈朝琴 宗华月 何奇玲
排版:黄泳琪
审核:刘伟
往期热点
国庆倒计时!重医er的假期关键词
秋日缤纷~一起点亮重医植物图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学校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
喜迎国庆丨祝重医师生国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