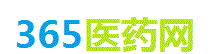牛奶蛋白过敏(CMPA)常见于婴幼儿,是由牛奶蛋白引起的异常免疫反应[1],可严重影响儿童的早期健康,给患儿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营养和生活质量负担[2],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对于改善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
近年来,CMPA 个体化分级诊疗已逐渐成为全球广泛关注和实践的诊疗理念。在 2024 年 10 月 10 日~13 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办的「第二十九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在西安召开。该次大会汇聚了国内外儿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儿科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热点问题。会议期间,丁香园有幸邀请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耿岚岚教授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斌教授围绕「CMPA 分级管理策略及母乳低聚糖(HMO)」展开精彩讨论,共享 CMPA 的诊疗经验及前沿研究成果。丁香园现选择重点内容编写成文,与读者分享。
图 1 第二十九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现场照片
图 2 专家对话 CMPA 的分级诊疗策略
EDA-OFC
是 CMPA 的诊断金标准
CMPA 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发病机制可分为 IgE 或非 IgE 介导,亦或两者混合介导。CMPA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症状及体征,严重程度不一,可累及皮肤、消化、呼吸等多个系统[2]。因此,耿岚岚教授指出,病史采集是临床上诊断 CMPA 的重要依据[1],病史询问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家族过敏史、牛奶蛋白来源及摄入量(喂养史)、过敏症状出现的年龄、过敏症状出现/持续/消失的时间等[3,4]。
因 IgE 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表现为进食后 2 小时内出现症状,并可参考过敏原检测,故容易判断;而非 IgE 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表现为进食后出现症状的时间不固定且较长,又缺乏实验室辅助诊断手段,故较难判断,往往需要通过试验性饮食回避-口服食物激发试验(EDA-OFC)来明确诊断。牛奶蛋白 EDA-OFC 也是诊断非 IgE 介导牛奶蛋白过敏的唯一可靠方法[1]。目前普遍的共识是[1]:针对牛奶蛋白 EDA-OFC 阳性患儿,通常 2 小时内出现症状,结合牛奶蛋白皮肤点刺试验(SPT)阳性或能检测到牛奶蛋白特异性 IgE(sIgE)者为 IgE-CMPA,如果摄入牛奶蛋白 2 小时后出现症状,通常 SPT 阴性或检测不到牛奶蛋白 sIgE 者为非 IgE 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
耿岚岚教授结合临床经验指出,当高度怀疑 CMPA 时,在 OFC 开始前应先进行牛奶蛋白回避试验,饮食中回避牛奶或奶制品 2~4 周,记录临床症状;若症状改善,考虑该患儿临床症状可能与 CMPA 有关,需行 OFC 确诊,激发过程中监测并记录相关症状,当激发试验诱发出症状,即可确诊牛奶过敏[3]。值得关注的是,OFC 费时、费力、家长与儿童的依从性差且因存在一定风险,故须在具有急救设备的医院内并由专业人员实施。对于曾发生过严重 CMPA 反应的患儿不宜进行激发试验。此外,还需警惕迟发型 CMPA,若短时间未能诱发出症状,医生应指导家长离院后继续观察患儿表现 2 周,并仔细记录症状,以免漏诊[3]。
谈及 CMPA 如何分级/分度,耿岚岚教授表示,根据临床表现可将 CMPA 分为轻中度过敏和重度过敏,但非 IgE 介导 CMPA 和 IgE 介导 CMPA 的分度依据不同。重度与轻中度非 IgE 介导 CMPA 的区分,以是否出现营养不良、生长迟缓、严重的贫血、低蛋白血症、严重的特应性皮炎为依据,如患儿存在这些症状则为重度非 lgE 介导 CMPA。而重度与轻中度 IgE 介导 CMPA 的区分则是以是否存在严重的过敏反应,如呼吸困难(如喉头水肿)或过敏性休克等为依据,即如患儿存在这些症状则诊断为重度 IgE 介导 CMPA[1]。
图 3 耿岚岚教授大会现场采访照片
不同严重程度的 CMPA
营养管理策略不同
自 2010 年起,国内外权威指南均强调 CMPA 分级管理的重要性[1-2,4-8],即对于轻中度及重度牛奶蛋白过敏患儿,营养管理策略是不同的。牛奶蛋白过敏患儿因无法进食整蛋白配方,需要选择低敏配方如深度水解配方(eHF)或无敏配方如氨基酸配方(AAF)进行营养替代[1]。
吴斌教授指出,临床上绝大多数患儿的牛奶蛋白过敏症状以轻中度为主,仅有 10% 左右患儿为重度过敏。目前国内外指南/共识普遍推荐 eHF 作为大多数 CMPA 患儿的治疗首选配方[1,2,8],而重度 CMPA 患儿建议使用 AAF 进行替代治疗。谈及配方的使用疗程,吴斌教授建议,配方应持续使用 6 个月或至患儿 9~12 月龄[1],具体到临床上,还应根据患儿的肠道损伤的程度、乳糖耐受情况进行抉择。
耿岚岚教授补充道,eHF 可使 90% 以上轻中度 CMPA 患儿明显改善过敏症状[4],其作为绝大多数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一线管理方案,可以从三大方面有效缓解患儿过敏症状并帮助患儿更好的追赶生长:
第一方面,eHF 中蛋白质被水解为短肽,而短肽是蛋白质在人体吸收的主要形式,其吸收率是游离氨基酸的 2~2.5 倍[9,10],令 eHF 更易吸收,可促进 CMPA 患儿正常生长发育。
第二方面,高渗透压配方可能会损伤患儿肾脏功能,引起各种胃肠道疾病,甚至可能引起大脑损害等[11]。eHF 的渗透压平均值为 243 mOsmol/kg,更贴近母乳 290 mOsmol/kg 左右的渗透压,而 AAF 渗透压的平均值为 328 mOsmol/kg[12]。因此,eHF 可以有效避免高渗透压可能会对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更易耐受。
第三方面,深度水解配方中保留的小肽能够提供更全面的营养,尤其是在免疫支持和肠道健康方面[13],可在改善过敏症状的同时早期诱导患儿产生免疫耐受,进而促进患儿生长发育。
但是,并非所有 eHF 都是一样的。不同 eHF 的营养成分与生产工艺各有不同,导致配方特性存在差异,如肽链来源、水解程度等均有所不同,而这些因素都可影响 eHF 疗效[14]。一项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 1200 道尔顿」的肽链比例范围从 67%~99% 不等,而「 1200 道尔顿」的肽链比例越高,配方的残存致敏性就越低[15],故应选择「 1200 道尔顿」肽链比例高的 eHF。因此,耿岚岚教授特别强调,应给 CMPA 患儿使用经过临床研究证实有效的 eHF。
回归本源
添加 HMO 的 eHF 带来额外获益
耿岚岚教授指出,HMO 是母乳中含量仅次于乳糖和脂质第三大固体营养物质,也是母乳中独特的生物活性成分,是促进生命早期免疫成熟的关键,对婴幼儿早期免疫功能发展具有重要支持作用[16-17]。
吴斌教授则表示,CMPA 患儿肠道菌群失衡,与健康婴儿不同,表现出厌氧菌增多,双歧杆菌等减少的肠道菌群紊乱状态[18-20]。而补充 HMO 可能会潜在地增加双歧杆菌,使 CMPA 患儿的微生物群组成更接近母乳喂养婴儿。此外,HMO 的免疫调节特性,包括与树突状细胞的相互作用和减少抗原-抗体复合物诱导的趋化因子释放,被认为在减轻 CMPA 患儿过敏症状和促进耐受性发育方面至关重要[21-22]。因此,在配方粉中添加 HMO,或可回归母乳本源,进一步完善婴幼儿 CMPA 的营养管理。
图 4 吴斌教授大会现场采访照片
但母乳中 HMO 种类多样,不同种类的 HMO 功能不同。耿岚岚教授指出,目前 2'-岩藻糖基乳糖(2'-FL)与乳糖-N-新四糖(LNnT)是母乳 HMO 中含量较高、也是研究较多的两种。基于丰富医学循证,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批准 2'-FL、LNnT 这两种 HMO,可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在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以及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中。目前已有临床研究证明[23-24],使用添加 2'-FL 和 LNnT(与母乳含量相当)的 eHF后,CMPA 患儿的肠道菌群模式更接近母乳喂养儿,黏膜炎症得到控制,过敏症状得到有效缓解,同时支持 CMPA 患儿正常生长发育以及降低感染风险。
小结
CMPA 是婴幼儿期较为常见的食物过敏,严重影响患儿健康。CMPA 分级诊断是给予合理营养干预的基础,随着疾病认知的深入、临床诊疗水平和观念的提升,开展分级管理可使患儿获得合理营养干预、实现最大获益。此外,添加 HMO 的 eHF 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促进免疫耐受等进一步优化 CMPA 患儿的营养管理。
专家介绍
耿岚岚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消化科主任
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
•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十八届委员会消化学组副组长
•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消化内镜学组副组长
• 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小儿消化微创学组副组长
•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儿童消化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 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营养学组组长
• 广东省医师协会炎症性肠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炎症性肠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华儿科杂志第十六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
▲上下滑动查看▼
吴斌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 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儿科学专业分委会委员
•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委员
•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儿科消化学组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药学会儿童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 福建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福建省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参考
内容策划:应岑
内容审核:徐超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 陈同辛,等. 中国婴儿轻中度非IgE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诊断和营养干预指南.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22,37(04):241-250.
[2]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新生儿牛奶蛋白过敏诊断与管理专家共识(2023)[J]. 中华儿科杂志,2024,62(1):12-21. DOI:10.3760/cma.j.cn112140-20231007-00257.
[3]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免疫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等. 中国婴幼儿牛奶蛋白过敏诊治循证建议[J]. 中华儿科杂志,2013,51(3):183-186. DOI:10.3760/cma.j.issn.0578-1310.2013.03.006.
[4] 陈同辛.婴幼儿牛奶蛋白过敏国内外指南解读——更好地识别、诊断和治疗[J].临床儿科杂志,2018,36(10):805-809.
[5] Fiocchi A,et al. Pediatr Allergy Immunol, 2010, 21( Suppl 21): 1-125.
[6] Venter C,et al.Clin Transl Allergy. 2017 Aug 23;7:26.
[7] Vandenplas Y,et al.Nutrients.2019 Jun 26;11(7):1444.
[8] Vandenplas Y,et al. J Pediatr Gastroenterol Nutr. 2024;78(2):386-413.
[9] Zaloga GP. Physiologic effects of peptide-based enteral formulas. Nutr Clin Pract. 1990 Dec;5(6):231-7.
[10] 唐少冉,周煦婷,侯晓莹,等. 二肽类代谢物生物学功能及分析方法研究进展[J]. 药学研究,2023,42(1):39-43,58. DOI:10.13506/j.cnki.jpr.2023.01.008.
[11] 贾宏信,苏米亚,陈文亮,等.母乳,配方乳渗透压及对婴儿健康影响研究进展[J].食品科学, 2021.
[12] 王文特,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渗透压的不同检测方法和结果比较分析[J]. 现代食品科技,2020,36(9):300-308,187.
[13] 朱俐光, 李中跃. 儿童食物免疫耐受形成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19,21(06):613-618.
[14] Chauveau A, et al. Pediatr Allergy Immunol. 2016 Aug;27(5):541-3.
[15] Nutten S, et al. Allergy. 2020 Jun;75(6):1446-1449.
[16] Bode L. Glycobiology. 2012, 22(9):1147-1162.
[17] Ballard O,et al. Pediatr Clin North Am. 2013; 60(1):49-74.
[18] Thompson-Chagoyan OC, et al. Pediatr Allergy Immunol. 2010 Mar;21(2 Pt 2):e394-400.
[19] Yang Y, et al. Front Microbiol. 2021 Aug 16;12:716667.
[20] Yu Z, et al. Microb Pathog. 2023 Oct;183:106329.
[21] Sekerel BE, et al. J Asthma Allergy. 2021 Sep 24;14:1147-1164.
[22] Walsh C,et al. J Funct Foods. 2020 Sep;72:104074.
[23] Boulangé C L,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3, 24(14): 11422.
[24] Vandenplas Y, et al. Nutrients. 2022;14(3):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