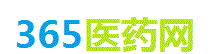在患者的口耳相传中,专家意味着拯救、希望、重生。在同行眼中,专家意味着荣誉、权威。而在现实中,专家意味着什么?专家何以成为专家?请关注仁心栏目,我们将呈现一幅“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名医群像,为您讲述那一个个荣誉与光环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联系上廖新林,说明采访原因后,他说自己此前已受过太多荣誉,如今又刚刚因高原病四级伤残已经病退,实在不适合再被宣传报道。再三劝解下,他终于答应跟39健康网谈谈从医31载经历过的那些惊心动魄,那些点滴温情,那些从传染病一线转向全科医生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以及他心目中的“医者仁心”。 廖新林,1988年毕业于湖南南华大学,先后在南华大学附属公共卫生医院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后响应国家发展全科医生的号召转向全科医生,调任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任门诊部主任。 他曾参与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救治前线,被感染后,度过半月难忘终生的隔离日子;也曾于2015年,广东省惠州市出现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病例后,作为传染病专家参与救治;2017年,他又主动申请成为惠州市第一批援藏医疗队队员前往西藏朗县,进行为期一年的援藏医疗工作。 感染“非典”:其实我也怕死 十六年前的“非典”事件,是一次因SARS病毒导致的,从我国广东扩散至全球的传染病疫情。它带走了多名患者的生命,也包括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它引发的恐慌至今残留在不少人心中。这其中,就有廖新林。 廖新林从未想过自己离死亡那么近。2003年,作为传染病医生,他从南华大学附属公共卫生医院北上,抵达北京呼吸道研究所进修,不久后,疫情传到北京。 由于资历较深,廖新林被派往救治前线。在北京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一位因抢救病人被感染“非典”的医务工作者痛苦地躺在床上,他知道自己患上了肺纤维化,一度不想活,扯掉气管欲自杀,守着他的正是廖新林与另外一位女医生。 “我俩就扑上去,给他接上气管。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就被感染了。”廖新林回忆起这段深刻往事时,略显激动,在电话那头的他提高了音量。 女医生病得较重,躺在病床上很久,而廖新林则出现了发烧等症状,也被隔离起来。在那痛苦的半个月里,他与外界隔绝,每天要做的事情只有一项:测量体温。上午8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其余时间,他只能待在隔离病房里,身为医务工作者,他明白一旦自己真的被确诊为“非典”,结局可能只有无药可医地死去。 “恐怖哦,哎呦,从那以后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了。虽然医务人员前仆后继,但不幸倒下来的也是真的可怜,我们也是人呐,也害怕。我们当然都希望平安回家。在那个时候才觉得生命的可贵。” 那段时间,廖新林独自一人思考了很多很多,想到了在湖南抗击禽流感的时候,自己全副武装看着关在小屋子的病人;想到自己干了15年的传染病,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会死在这里。 他坦言,自己的确退却了,决定度过危机后,在北京多学些知识,转向全科医生。“刚好那时候国家鼓励做全科医生。” 从“非典”中活过来的廖新林,开始学习心内科等医学知识,并在北京、广东等国家级医院进修、成长。他说自己不怕别人笑他不勇敢,“我愿意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我也怕死。” 报名援藏:我怕以后没机会 2008年,廖新林被调往广东惠州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任内科副主任医师。 而在从广东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2017年,他做出了援藏的决定。作为惠州市首批援藏医疗队里唯一的60后,身边有人说他年纪大了,小心高反,得高原病。廖新林回说,如果再不去,以后就真的去不了了。 他对西藏有向往,知道那里的医疗条件差,藏族百姓缺医少药。年轻时虽然去旅游过,但他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以医生的身份去一次,去为那里淳朴的百姓做些什么。 没想到,一到惠州市对口援藏的林芝市朗县,廖新林就受到了来自高原的“下马威”。 “一去就气喘,比如拖个地板都出气不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制氧机,”在平均海拔3700的朗县,高原缺氧导致无法入睡也让廖新林倍感痛苦,“幸好我们带了40颗安眠药过去,开始时靠安眠药控制自己的睡眠。” 于是,在这初上高原的日子,廖新林和同事们几乎只能边吸氧边工作,甚至不吸氧无法入眠。 说起援藏期间做了哪些事,作为医疗队队长廖新林的话匣子彻底被打开了,电话那头的他开始细数起他与队员们两年前挥洒在高原的热血故事。 他们将年久不用、堆满灰尘的手术室重新启用;又开展了无痛胃镜业务,填补了当地空白,将舒适化医疗带给藏区百姓;急诊科得到改建,让当地需要抢救的百姓能先留住一口气,不至于发生病人死在转运车上的事情;凭着在传染性疾病方面的专业经验,朗县卫生服务中心的感染性疾病科也得到重新规范化建设...... 对于发生在西藏的点点滴滴,廖新林记得无比清楚。去到五千米海拔的雪山上义诊的事情令他难忘至今。 原来,为了挖虫草,当地牧民会在每年的虫草季节爬到五千米寒冷缺氧的雪山上住三个月。他们住的是漏风的铁皮屋,生病了也不敢下山,就怕耽搁挖虫草的时间。 听说了这个消息的援藏医疗队决定一起上山为他们送医送药。“上山的路就跟韩红所唱的天路一样,崎岖不平,而旁边就是万丈悬崖。越往上走高原反应越重,连说话快一点都呼吸不畅。”廖新林告诉39健康网。 天气更是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透,义诊那天上午还是烈日炎炎,到了下午就突然飘雪,气温骤降。“当时太阳很大,晒得我们恨不得穿短袖,但是后面快结束的时候,一阵阴风过来,一朵朵雪花飘下来,我的脸和嘴巴都乌了,村长赶紧把我送上去吸氧,那天去了半条命,才知道人要敬畏高原。”回忆起海拔五千米的义诊,廖新林仍觉后怕。 在西藏的日子过了一半的时候,廖新林身体的不适越来越明显。身为队长,他直面创二级医院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年龄较大,他不断出现高原反应,经常头痛,失眠呕吐,后咳嗽日渐严重,被林芝人民医院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高原病。短期调整后,他又主动返回朗县。 最后,为了身体,廖新林提前几个月返回广东修养治病。没有坚持到和队员们齐齐整整地在一年援藏期结束时返回一直是他心中的遗憾。 如今因高原病提前退休的他,回想起当初的决定也不曾后悔过。“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即使患上高原病,我也从不后悔支持援藏工作,就是很遗憾身体原因不得不中断,有机会,我会再去看看那美丽的高原,再为那些纯朴的藏族人民做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他说这段援藏经历是一次神奇的体验,他会一直记得那片自然、动物和人和谐相处的圣地,也会记得那淳朴善良的人。 作为医生:要有救死扶伤之心,也要有体谅心 廖新林成为一名医生的理由很简单——生病的父亲。 “当时我父亲阑尾穿孔,因为找不到医生差点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后来,父亲要求下我选择医学专业。想到从医后可以解除病人们的病痛,甚至拯救他们的性命,我觉得医生很神圣和伟大,所以走上了这条学医之路。” 在廖新林看来,一名医生的“仁心”体现在“救死扶伤”和“体谅心”中。 “救死扶伤”是抗“非典”带给他的体悟。以前的他并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是那次的经历让他发觉原来医生的使命感原来这么强有力,可以让一个人不畏惧生死,挺身而出。 而从传染病防控专家到全科医生,他则学会了从点滴之间尽医生之责。面对重新的学习与挑战,面对多疾病的知识和多几倍的病人,他慢慢从这个角色中找到自己。 与以往只需治疗传染病不同,全科医生在门诊中兼顾的更多,除了治疗身体的各种疾病,还要兼顾患者的心理问题。 有时,门诊里碰到情绪比较激动,甚至口不择言的患者,廖新林总说,作为医生,其实更应该体谅患者的痛苦,“他们抱着期望之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给他治好病。只要以心比心,患者也会明白医生的苦心。” 成为全科医生十余年来,廖新林发觉自己的成长,“我变得更柔软,也慢慢学会找到更合适的与患者的沟通技巧,这么些年下来,我觉得我也蛮适合做个全科医生的。” 注:患者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撰稿:杨乔